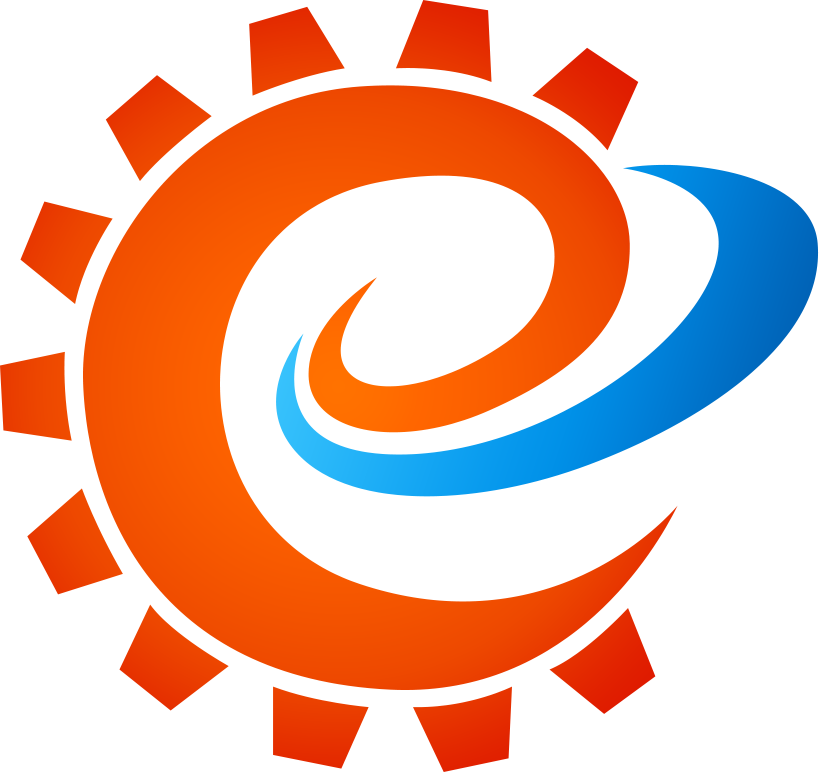我曾用十块钱丈量整个世界——八块给猫,两块留给自己。
那是一段关于贫穷、依赖与失去的日子。猫的呼噜声是我最温柔的夜曲,也是一场缓慢崩塌的前奏。
当爱变成习惯,信任开始破碎,连最微小的温情都可能在日光下消散。
那十块钱,是我世界的度量衡,也是后来崩塌的尺度。
八块,是它的。两块,是我的。
它刚来时,像一页被雨水浸透的旧信纸,蜷缩在纸盒的阴影里。纸的纹理早已模糊,只有一点点残存的笔迹,似乎写着某段被遗忘的温柔。我用那八块钱换来最便宜的猫粮,看它小口啄食。那细碎的咀嚼声,如雨滴落在铁皮屋顶,是我贫瘠日子里唯一的回响。
剩下的两块钱,支撑着我寡淡的胃,而它全然依赖的眼神,则慢慢滋养着我那片早已荒芜的心田。
我给它洗澡。水流在它细瘦的脊背上滑落,指尖触及那层薄薄的骨骼,像摸到一根颤抖的弦。它的体温一点点传来,呼吸微弱却笃定。那湿漉漉的信任,沉甸甸地压在我掌心。夜晚,它蜷在我脚边,呼噜声是唯一的潮汐,轻拍着我们共筑的、看似坚固的沙岸。
第一次带它去公园,是命运暗中的转折。风很轻,草叶还带着露珠。一块陌生的猫粮落在地上,它迟疑片刻,还是低头吞下。我唤它,它只是甩甩尾巴。那一刻,薄冰之下,传来一声低低的脆响——细微得几乎听不见,却在我心底长久回荡。
起初,它只是偶尔溜走,嗅闻那些陌生的馈赠;后来,每一次出门都成了一场对我的审判。我的八块钱世界,在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食面前,一寸寸褪色。
我开始更努力——削减自己的餐食,只为换得更香的罐头;深夜在超市货架前反复权衡,只为给它一个更好的明天。可它吃得越来越挑剔,我的期待被一次次冷淡的回眸碾碎。那天,它焦躁地望着窗外——楼下,一个提着塑料袋的身影正缓缓走过。
它甚至没有看我一眼,便纵身跃下,奔向那份司空见惯的施舍。
我看着那碗几乎未动的食物,心里那层由无数次微小背叛累积的厚茧,仿佛被瞬间刺穿,流出无声的、冰冷的绝望。那些路人给予的是即兴的甜,而我付出的,是渗透在每日清水与粮食里的、缓慢的责任。它选择了更轻松的那一种。
手腕与手背上细密的抓痕,是它一次次挣脱我、奔向“自由”时留下的印记。从无意的划伤,到清晰的抗拒。最后一次,它为了一块路人抛出的零食,用尽全力挣脱。利爪划破皮肤,血珠顺着掌纹滑下,在地板上开出一朵暗红的花。那一刻,我心里那簇摇曳已久的火苗,“噗”的一声,熄了。
我没有再看它,也没有试图去抱它。空气在我身后合拢,像一扇缓缓关上的门,隔绝了它,也隔绝了那个曾倾尽所有的自己。
后来重逢,它脏兮兮地跟在我身后,叫声嘶哑。它还记得我,这个曾带它回家的人。可我,已经不要了。
我关上门,将它连同我们所有的过去,一起关在门外。它的叫声穿过门缝,像一把生锈的锯子,一下一下,锯着我仅存的感知。很疼,但那疼,是清醒的。
那天下午最后一缕阳光淡得像纸,铺在地板上。我看着自己的影子,在空荡的房间里被寂静一点点吞噬。
门外安静了很久。
我以为风停了。
后来才知道——
是心,不再动了。